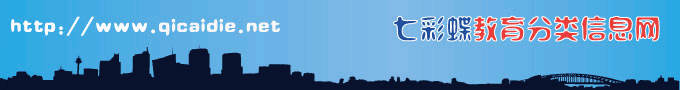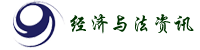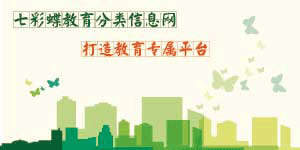佛教:净土宗居士袁宏道的佛学
在古代的明朝时期,公安三袁皆好佛,兄弟三人曾在北京崇国寺结蒲桃社,研究佛学。而其中最特出的是袁宏道。

他有诗说:“一榻书和卷,三生钵与衣。尘劳方未己,合掌愿皈依。觉路昏罗彀,禅灯黑绛纱。早知要世网,悔不事袈裟”,表达了自己向佛教真诚飯依的心情。
作为一个文学家,袁宏道却著有《西方合论》、《德山尘谭》、《金屑编》、《六祖坛经节录》、《宗镜摄录》)等佛学著作。
其中,《西方合论》被明代高僧智旭列于《净土十要》。而《金屑编被李贽大为推崇,赠诗相赞:“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劳苦。”

在李贽的童心说影响下,袁宏道提出了“性灵说”,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自由清新的诗文风格,成为明末公安文学的主帅。
“性灵说”这一理论,是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一文中提出的。他形容其弟袁中道的文字:“大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
这样情之所至的文字,就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真诗”:“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袁宏道还称赞了文人一向所鄙视的民间通俗文学,其理由也是这些作品都是“真人”、“真声”:

“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而且“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重视人的天然本性和情欲的抒发,这些观念都鲜明地显出李贽的“童心说”的影响,都与禅宗的“心性”理论是相关的。
在佛学观念上,袁宏道起初受李贽影响很大,倾心学习李贽的“狂禅”,当有人讥讽“狂禅”是一种“取相”时还为之辩护(因为大乘佛教讲诸法空相)。他认为,禅是变动而没有定法的,相应的,也不必拘泥佛法,佛也是人而已,“自不必以佛法为案,且佛亦人也”。

当然另一方面,袁宏道对狂禅过滥的缺点也有认识,“弟往见狂禅之滥,偶有所排,非是妄议宗门诸老宿”,加上李贽观念激进,容易招致守旧人士的攻讦和迫害,这也使袁宏道从狂禅的热烈信奉者,后来转向净土宗,主张禅净双修,并且一度断肉禁欲,持戒修行。
万历二十七年冬,袁宏道著《西方合论》,是他对自己的净土信仰的一个总结,也成为明末净土宗的重要著作。

不过修行一段时间净士后,袁宏道又开始复归禅宗,万历二十九年,袁宏道对过于艰苦的“持戒精进”生活发表看法说,“此饮药而服忌,不若不饮之愈也”。
他开始学习洪州、临济禅学,主张安心任运的随缘禅—“知法无性,所以不断一切法,是谓从缘起也”,“随缘消日月,任运著衣裳,此临济极则语,勿作浅会”。
对于净士信仰抑制个人情欲严格持戒,袁宏道说要“打倒自家身子,安心与世俗人一样”。他于万历三十二年所著的《德山尘谈》,就是这种随缘禅思想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