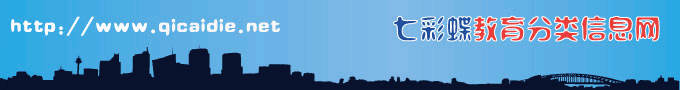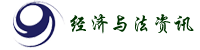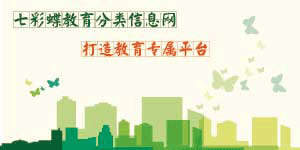那些能让我们生病的动物,在人类生活区活得更好
来源:Nature自然科研
将自然生境转化为人类用地是否更利于那些携带致病病原体的动物?对于这个紧迫的问题,一项关于脊椎动物的全球性分析做出了回答。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人类改变了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宜居地。森林、草原和沙漠转变为城市、郊区和农田,导致许多物种减少或消失,而另一些物种却蓬勃发展。输家往往是生态特化种(specialist),如犀牛或鸵鸟,它们具有高度特定的进食或生境要求,而且比非特化种相对体型更大、更稀有、更长寿。赢家往往是那些体型小、数量多、寿命短的泛化种(generalist),如老鼠和椋鸟。

Gibb等人在《自然》上撰文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些赢家比输家更有可能携带致病菌(病原体)。因此,当我们将自然生境转为人类用地时,我们无意中增加了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传播概率,这类疾病是由可以从动物跳到人类身上的病原体引起的。
几十年来,土地使用变化增加了人畜共患疾病风险的例子越来越多。例如,在其他物种已经消失的人类主导景观中,盛行着某些啮齿类动物,它们会增加南美锥虫病(查加斯病)、若干蜱虫病和一系列所谓的汉坦病毒病的致病病原体数量。但是,这种模式的普遍性及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仍有争议。
Gibb及其同事在全球尺度上调查人类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是否有利于最有可能导致疾病的脊椎动物物种时,必须克服两个障碍。一是沿着从未受干扰的自然生境到人类主导地区的梯度,确定哪些动物物种趋于消失,哪些趋于繁盛。作者利用PREDICTS项目(Projecting Responses of Ecological Diversity In Changing Terrestrial Systems | https://www.predicts.org.uk/)的数据库完成了这项工作。数据库包含了来自666项研究的320多万条记录,这些研究沿着世界各地的土地利用梯度对动物进行了统计。

第二个障碍是确定这些物种中哪些携带有可以感染人类的病原体。为此,Gibb等人汇编了6个包含宿主-病原体关联的数据库的信息,发现3883种脊椎动物宿主物种和5694种病原体之间有20382个关联。遗憾的是,发现一种动物和一种病原体有关联并不一定表明该动物可以将病原体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动物。认识到这一点后,Gibb及其同事使用了更严格的标准来确定宿主与病原体之间的关联,包括确定是否有直接证据表明宿主体内存在病原体,以及宿主传播病原体的能力。
作者从这些分析中发现了惊人的模式。随着以人类为主的土地利用的增加,人畜共患病宿主的总数也在增加,而非宿主的总数却在减少。在土地利用较密集的地区,宿主物种的数量和这些物种的个体数量都增加了,而后一种的影响更强。啮齿类动物、蝙蝠和鸣禽的数量在以人类为主的地区显著增加(图1)。对食肉动物和灵长类动物的个体数量影响较小。然而,如果缺乏深入的研究工作,导致无法检测到人畜共患的病原体,则宿主物种可能被误归为非宿主物种。考虑到这一点,Gibb等人在分析中加入了一个叫做“自助抽样法”(bootstrapping)的统计过程。这使他们能够使用一种纳入了已发表的关于某物种的研究数量的方法,将非宿主重新划分为宿主。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仍然是一样的。
![图1|城市街道上的一只老鼠。Gibb等人[3]报告称,携带有可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的脊椎动物,如啮齿类动物,在经人类改变的景观中繁盛发展。来源:Alamy](https://n.sinaimg.cn/tech/crawl/162/w550h412/20201006/4354-kaaxtfn1614760.jpg)
图1|城市街道上的一只老鼠。Gibb等人[3]报告称,携带有可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的脊椎动物,如啮齿类动物,在经人类改变的景观中繁盛发展。来源:Alamy
由动物源冠状病毒引发的COVID-19大流行,让全世界认识到人畜共患疾病对人类的威胁。伴随着这种认识,产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错误认知:野外自然是人畜共患病的最大来源。将丛林描绘为充满微生物威胁的流行文化以及一些早期的科学研究强化了这种观点。Gibb等人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纠正意见:最大的人畜共患病威胁出现在自然地区被改造为耕地、牧场和城区的地方。
在人类占主导地位的景观中繁荣生长的物种,往往是那些构成人畜共患疾病威胁的物种,而减少或消失的物种往往是无害的,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动物对人类干扰的适应能力是否与它们承载人畜共患疾病病原体的能力有关?Gibb等人发现,因人类土地利用而数量增加的动物不仅更有可能成为病原体宿主,而且更有可能携带更多的病原体物种,包括更多的能感染人类的病原体。
一项最新研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同样的一般性问题,发现日益广泛和丰富的哺乳动物携带的人畜共患病病毒,比正在减少、受威胁或濒临灭绝的哺乳动物多。这些观察结果支持以前的研究——展现了与生态复原力相关的高繁殖率和与较低病原体负荷相关的免疫系统高投资之间的权衡。换句话说,具有类似于老鼠的生活史的生物似乎比其他生物更耐受感染。另一种非排他性解释是,泛化种病原体(更有可能外溢至新的宿主)倾向于通过适应,靶向它们最有可能在演化进程中遇到的宿主。这些宿主是世界上的老鼠,而不是犀牛。
Gibb等人的分析表明,恢复退化的生境和保护未受干扰的自然区域将有利于公众卫生和环境。展望未来,对已知的和潜在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监测,如果集中在人类占主导地位的景观上,可能会最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