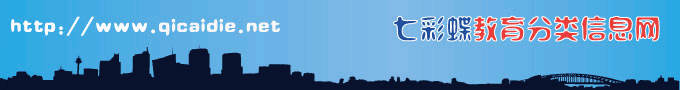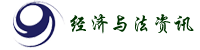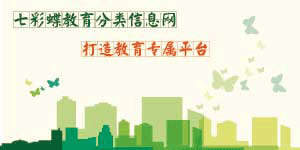青灯犹在读书檠
父亲是老三,十六岁便接过家里的犁,本该读书的年纪,却在田里辨节气、灶房学做饭,将“读书”二字埋进心底。四叔想当兵,因张家已出两位军人未能如愿,最终也扛着锄头,与父亲一同把日子种进土里。
每年除夕,张家桌上总有多碟芥菜。祖父夹给大伯、二伯,声音醇厚:“芥菜寓意一清二白,你们在外做事得心里亮堂、手脚干净。”目光扫过父亲与四叔,既有歉疚更有期盼:“你们守家辛苦,要教孩子多认字读书。”
我对书的执念,便是在此时生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找书比找人参还难。第一次接触课外书,是二伯家卷边的连环画《十兄弟》,油墨混着旧纸霉味,却让我爱不释手。
小学二年级,老师要求买的作文选成了我的“文学启蒙”,书中句子被我抄满作业本。我还缠着父亲买《新华字典》,他摸出卖十斤红薯换来的五毛钱。这本绿壳字典被我视作珍宝,一年下来页脚卷成波浪。
后来买了《成语词典》,“卧薪尝胆”“凿壁偷光”的故事让我着迷。那时村里没通电,每晚家人睡后,我便点煤油灯夜读。昏黄火苗跳动,煤油味呛得嗓子疼,灯芯结渣就用针挑掉,借着微光再读几页。
读书的胃口一旦勾起便收不住了。十来岁时,我在二伯家木箱里翻出线装版《水浒传》《三国演义》,竖排无标点的文字,我连蒙带猜地读。用三个鸡蛋换得《射雕英雄传》借阅权,三天便看完;后来用半年压岁钱买了《红与黑》《鲁滨孙漂流记》。
或许是书读得多,我的语文成绩从小学到大学稳居班级前茅,作文常被当作范文。后来做领导文字秘书,写材料能拿捏分寸,皆得益于儿时“啃”字典、“嚼”成语的底子。
爷爷的孙辈中,“苦学”者不止我。大伯的儿子聪哥,三岁患小儿麻痹症无法站立,却对书充满渴望。每年寒暑假,大伯上班前将他背到新华书店,店员特意给他留了角落位置。直到十九岁离世,聪哥留下八十多本工整笔记,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大伯的女儿星姐考上中专时,全村轰动。二伯的女儿华姐,是姊妹中第一个大学生。她寒冬腊月披着旧棉被在煤油灯下苦读,手冻得通红仍写着工整笔记。她说,拼命读书是想看看“山外面的天”,最终考上医学院,用手术刀救死扶伤。
我与四叔的女儿燕妹同岁同班,从小学到高中一路“比学赶超”。我们一起在煤油灯下做题、田埂上背课文、攒钱买《读者文摘》轮着看。最终,我考上本省大学,燕妹去外省读师范。
大学里我学化学,却常去中文系听课,课余泡在图书馆。每晚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读《围城》《烦恼人生》等书。
后来我当了两年支教老师,把书中的道理讲给山里孩子听;再通过公考到省城基层工作,换过六个单位、跨三个市州,无论住哪,桌上总摆着台灯,睡前必翻看几页书。看着熟睡的儿女,便想起祖父的期许、聪哥的笔记、华姐的书信——“读书”已成张家新“祖训”。
黄庭坚诗云:“身如陌上狂风过,心似夜来新月明。桑户居然同物化,青灯犹在读书檠。”如今我带儿女读书,教他们认《新华字典》,讲《十兄弟》的故事,在台灯下共背古诗——那盏照亮我童年的“青灯”,又在儿女们的书桌前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