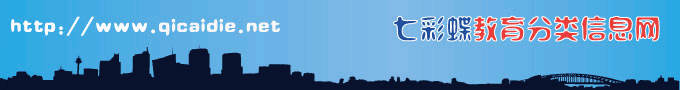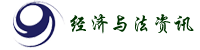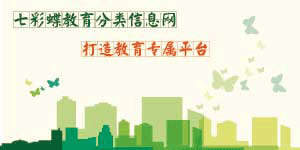大乘佛法入汉来——鸠摩罗什与北凉石塔
“菩提”“因缘”“烦恼”“极乐”“苦海”“爱河”“心田”“神通”“大千世界”“一尘不染”……这些佛教相关的汉语词汇在当下被大众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如今看来已然稀松平常,但早在千余年前,它们的出现却是翻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些词汇本不存在于中土,是高僧鸠摩罗什为了将梵文佛经翻译成汉字文本而创造,既谐了梵语的读音,又合了汉语的文意,可谓十分精妙。这样的词汇,鸠摩罗什创造了数百个。
龟兹 · 佛国俊才
说起鸠摩罗什,就不得不提及他的出身。
从他的名字不难看出,鸠摩罗什并非汉人,不过,他是个未出生时就与佛有缘的孩子。他的父亲鸠摩罗炎本是天竺国国相之子,出家东渡到了龟兹。龟兹在天山南麓(今新疆库车一带),在当时的西域诸国中算得是个相当富饶兴旺的国度,举国笃信佛教:“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项。王宫壮丽,焕若神居。”龟兹国王白纯想要留下鸠摩罗炎做国师,强行令他还俗娶了王妹耆婆公主,生下了鸠摩罗什,罗什就是在这样具备着浓厚佛教氛围的王室家庭长大。
据说耆婆在怀有罗什时,记忆力与理解力陡然大增,还突然无师自通了天竺语,辩经水准碾压众人,让大家惊叹不已,罗汉达摩瞿沙说“此必怀智子”,是因为罗什在母亲体内的缘故,并将罗什比作佛陀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后来耆婆果然在生下罗什后又将这些知识尽数忘却——这或许是时人为了神化鸠摩罗什的说法,但罗什的聪慧颖悟却是毋庸置疑,他半岁开口,三岁识字,五岁便博览群书。罗什七岁时,耆婆突然在一次郊游时看到荒坟白骨而勘破红尘,这个原本就信奉佛教的公主在丈夫还俗后,自己却出了家,还带着长子罗什一道皈依了佛门。
当时比较流行的佛教教派是小乘教,鸠摩罗什随同母亲前往罽宾国拜师槃头达多学习的也是小乘佛法,彼时年方九岁的罗什已然能够“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轻松辩经折服外道论师,崭露头角,槃头达多亦颇为这个弟子自豪。
《晋书》列传第六十五 晋书九十五“鸠摩罗什”[唐] 房玄龄 著 百衲本
然而,罗什十二岁这一年在返回龟兹的途中结识了大乘教的高僧须利耶苏摩,在其带领下通读《中论》《百论》《十二门经》等大乘经典后,恍然大悟,感慨与大乘佛法相比,从前学习小乘佛法“犹如人不识金,以矿石为妙”,毅然改入大乘教。槃头达多得知后,找到鸠摩罗什想要劝得意门生“迷途知返”,却在与罗什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辩经后被罗什说服,昔日的师父成了徒弟,反过来向罗什学习大乘佛法。
其实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的区别,简单来说,便是小乘渡己而大乘渡人,鸠摩罗什在十二岁便能有普度众生的宏愿,或许这也就是为何他未来能在凉州度过那些岁月的原因,这是后话。
除了大乘佛法外,在游学西域诸国的日子里,鸠摩罗什博览群书,还对文韵、工艺、历算、医药、天文等众多学科颇有钻研,这使得他小小年纪在西域便已声名鹊起。二十岁受过具足戒后,罗什正式成为了一名比丘僧,接过了父亲的衣钵,被奉为龟兹国师。龟兹国王对他十分礼重,为他打造金狮子座,西域诸王也多闻鸠摩罗什神僧之名,“长跪坛下,以身为阶”,请罗什登坛说法。
汉唐丝绸之路流通的龟兹五铢钱 图源: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2年第2期·总第238期《龟兹五铢钱考——兼论公元前5世纪至7世纪丝绸之路流通货币》
这一年,耆婆决定前往天竺继续游历,在与罗什分别时,耆婆为这个注定不会平凡的儿子未来的命运担忧:“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大乘这样高深的佛法,怕是要靠你去传扬到中原了,但这件事对你无益,如何是好?)”罗什则答道:“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曚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若能使大乘佛法流传东土,造福人间,让迷茫的众生醒悟,即使遭受炉镬之刑,我亦无怨。)”这个年轻的僧人虽然出身富贵,但早有舍身救世的觉悟。
凉州 · 玉汝于成
很不幸的是,耆婆的预感终究变成了现实。
随着鸠摩罗什“道震西域,声被东国”,中原大地也闻听了他的名号,中土的名僧道安对这位西域高僧十分推崇,极力向当时的雄主苻坚建议迎请鸠摩罗什东行。苻坚听取了建言,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苻坚派手下大将吕光出兵龟兹,点名要他把鸠摩罗什送到自己身边——当然,除了苻坚本身信奉佛教之外,也暗藏了他的政治目的,鸠摩罗什在西域诸国颇具影响力,如果有他在,拿下西域自然更加容易。
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吕光攻破龟兹后,不仅西域臣服、罗什在手,还掳掠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俨然已有不可一世的架势。在他志得意满地带着“战利品”到达凉州时,旧主苻坚兵败被杀的消息传来,吕光顺水推舟,干脆原地称王,建立了后凉政权。
吕光和苻坚不一样,他是个打打杀杀的武将,不信佛教,更无一点对鸠摩罗什的欣赏,在他看来,当地百姓对于这位高僧的尊重无疑是一种对自己的不敬。吕光开始以各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折腾罗什,让他骑上恶牛劣马穿行于闹市,看他被摔到地上的狼狈之相犹嫌不足,又用烈酒将鸠摩罗什灌醉关进密室,强迫他与龟兹公主破戒,妄图彻底摧毁这位高僧的自尊和名望。
在经历过百般折辱之后,令吕光意外的是,鸠摩罗什并未因此消沉自毁,还好心向他警示了洪水的预兆。吕光自然不信,但当山洪真的暴发之后,看到罗什彻夜为伤亡的将士念经超度,他才对这位高僧另眼相看。
诚然,鸠摩罗什的内心未必真如外表看上去那样安然自若,对于自小出家的他来说,肉体受到的伤害无非是对臭皮囊的考验,但破戒娶妻这件事,不管对于他自己还是对于僧界、民众而言,想来都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但他应该还记得当年对母亲说过的话,为了把佛法带到汉地,为了让佛法造福百姓,无论吕光如何迫害,他都一一挺了过来,并把这些苦难当作是佛祖对他的试炼和自身的一场修行。哪怕吕光对他有所改观,还为他在凉州兴建了鸠摩罗什寺安置,但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能够卜问吉凶的工具人和宗教吉祥物而已,吕光父子本身依旧不信佛教,鸠摩罗什面对这样的政治主宰者,“无所宣化”,又不得自由,凉州于他是一个无法逃脱的金丝牢笼,这个牢笼,他一呆就是十七年。
熬过了自己心里的那一关,从年少时以弘扬佛法为本愿的鸠摩罗什自然不会轻易言弃,凉州虽是囹圄,但也是他此生磨砺与沉淀之地。
在凉州羁留期间,罗什开始系统学习汉语、阅读汉字典籍,甚至连《道德经》《庄子》等道教书籍也有所涉猎,了解到了汉人的语言节奏和文学韵律——这为他将来的译经大业打下了夯实的基础;此外,他还让自己融入民间,与当地百姓交谈,学会了凉州方言,也接触到了汉人的生活习惯和基本礼仪,这使得他在讲经时可以因地制宜,用汉人传统的“孝文化”作为切入点,让当地百姓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佛家经典,比如《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他用最简明易懂的话向民众解释了“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的道理。
宝珠在黑夜里也能绽放光华,即使在这般难堪的境地,即使不能公开传法,鸠摩罗什的人格魅力依旧吸引到了大批信众,有些僧人甚至千里迢迢从中原西行而来拜他为师学习佛法,其中就有被后世赞为“秦人解空第一”的僧肇,他也是最早追随罗什翻译佛经的弟子之一。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唐咸通九年刻本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是的,其实在鸠摩罗什进行大型译经活动前,早在凉州之时,他就开始了初步的译经工作,《坐禅三昧经》《妙法莲华经》《弥勒成佛经》《富楼那问经》的译本是在凉州完成,《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首楞严三昧经》的异译本是在凉州搜集而来(后在长安重译)。或许在他用凉州方言向贩夫走卒讲解“诸法空相”之时,这颗种子就已经萌芽,这也是在一众译经大师中,鸠摩罗什的译本尤为文辞简练、义理通达、流传久远的原因。他将胡本、梵本翻译成秦本(汉本),目的就是能让更多人读懂佛经,当年改学大乘佛法所发下的宏愿,他始终没有忘却。
长安·大乘朗照
后秦君主姚兴在多次向吕光提出要迎鸠摩罗什来秦遭拒后,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发兵后凉,其时吕光已死,吕隆不敌而归顺,笃信佛教的姚兴遂以国师之礼恭请罗什前往长安,时年五十七岁的鸠摩罗什终于走出了凉州。
姚兴生性仁慈,待鸠摩罗什亦礼遇有加。他为罗什在逍遥园的千亩竹林中建造草堂寺,作为国家背书、提供资金和人力的官办佛教译场,由鸠摩罗什作为译主,另派了八百名僧人协助,规模之宏大,在历史上还是头一遭。除了姚兴派去的帮手外,四方僧众听闻罗什在长安译经,都纷纷奔赴而来,拜师学道,据说弟子最多时可达三千人。
在翻译经典时,鸠摩罗什遵循“重达旨、重文体”的原则:“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他不拘泥于原文格式,而是融会贯通,用意译的手法将其以汉字五言形式表达出来,有些在中土并不存在的概念,他则充分发挥想象、运用自己所学的汉学知识,创造出最贴近原义的词汇。除了新译之外,他也会重译一些前人流传下来过于拗口晦涩的译本,比如他所译的《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辞藻优美,朗朗上口,已成定译,后来明代才子唐伯虎的“六如居士”之号就取于此句。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东汉] 鸠摩罗什 译 [宋] 敦煌抄本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在长安的十二年里,鸠摩罗什率领僧众一共翻译佛经七十四部共三百八十余卷,其中大多都被后世奉为经典,传播之深远无可超越,居中国佛教史上四位译经大师之首而无愧。
与鸠摩罗什几乎同时期(略晚)的北凉石塔,四方塔座、八面塔身、覆钵塔顶,这种多元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独特塔型,可以在天竺窣堵波、阿旃陀支提塔、犍陀罗奉献塔等原型上找到类似结构,亦有学者认为受到了中原道教八卦图案的影响。而塔身上所刻神像、佛像、菩萨像,都与当时大兴修建的石窟造像相似,其容貌、着装、配饰等都有着浓厚的中原本土化倾向,可见在当时的民间,西来的大乘佛教已经与东方的中原文化产生了深度融合,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一座小小石塔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足以说明鸠摩罗什在大乘佛法“传之东土”的努力没有白费。
北凉石塔 北凉 1969年石佛寺湾出土(军分区旁)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
鸠摩罗什在临终前告诉众弟子,当以他的译经著作为重,勿学他个人品行,以臭泥莲花作喻,要他们“但采莲花勿取臭泥”。其实纵观鸠摩罗什之一生,始终像自己所译《金刚经》里说的那样,“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两次破戒均为形势所迫,唯有一颗弘法之心八风不动,他又何过之有?鸠摩罗什带给这个世间的,是慈悲、是拯救、是广阔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是积极的精神影响和寄托,他一生译作,是天竺和华夏两大古文明交汇的桥梁,是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史上无法逾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