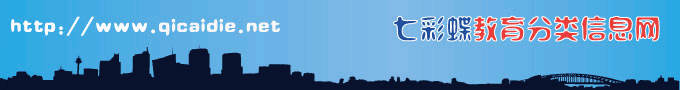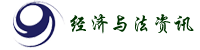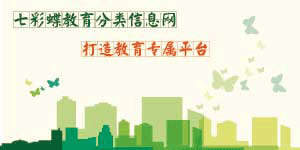《宴遇永安》藏着文化细节
一场聘猫礼“小明”登场
该剧改编自晋江文学城樱桃糕的热门小说《长安小饭馆》,讲述现代人意外穿越到古代,在永安城经营小饭馆,并与京兆少尹林晏(李昀锐 饰)以美食为纽带相知相守的故事。 收养三花猫“小明”时行的 “聘猫礼”,成了名场面:二人备好小鱼干等聘礼,男主还亲手书写了一张图文并茂的“纳猫儿契”。
“小猫咪,你是路过我家,还是要留在这里呀?”面对女主的疑问,林晏笑着给出充满仪式感的答案:“若想知道它的答案,行聘猫礼就可以。”他在契文中写道:“若它吃了你准备的聘礼,就是愿意做你的猫”,待三花猫吃下小鱼干后,又补了句“此后汝不必浪迹,不必捕鼠,不必守夜,此契为证,天地共鉴”。这段既有童趣又含古韵的情节,不仅让观众感受到古人对猫的珍视,更成了推动男女主情感升温的关键伏笔。
古人“纳猫”有多讲究?
不少观众好奇,这一仪式是否为剧情虚构?记者采访到著有《中国撸猫简史》的文史作家侯印国,他表示:“剧中的聘猫礼并非凭空创作,自宋代起,民间‘买猫添猫’就是件讲究事,当时称‘聘猫’或‘纳猫’,流程完备到堪称‘纳猫如纳妾’,元代典籍《类编历法通书大全》(卷九)中‘纳猫犬’条目下,就明确记载了宋代流传的‘相猫儿法’‘纳猫吉日’‘猫儿契式’,足见其仪式感早已制度化。”
宋代人聘猫,第一步便是 “择良辰”,其重视程度堪比婚嫁、迁屋等大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丁集)明确指出:“取猫吉日:天德、月德日,切忌飞廉日”;《类编历法通书大全》则记载得更细致,不仅要求选天德、月德、生炁日,还需避开飞廉、鹤神所主方位——飞廉在道教中属 “大煞”,所到之处忌兴工、嫁娶;鹤神巡游时也会带来灾殃,需刻意回避。而具体到“接猫”的日子,宋人更偏爱“甲子、乙丑、丙子、丙午、丙辰、壬午、庚午、庚子、壬子”这些干支日,认为能为家宅带来吉祥。
选好吉日,下一步便是“相良猫”,宋代人早已总结出一套实用的“相猫法”。宋代陆佃在《埤雅》中记载:“狸身而虎面,柔毛而利齿,以尾长腰短、目如金银及上腭多棱者为良”,核心是挑“能捕鼠、身体壮”的猫。当时还流传着两首相猫歌诀,进一步细化标准:其一为“猫儿身短最为良,眼用金银尾用长。面似虎威声要喊,老鼠闻之立便亡”,强调体型、眼神与气势;其二是 “露爪能翻瓦,腰长会走家。面长鸡种绝,尾大懒如蛇”,点明需避开“腰长、尾大”的懒猫。至于毛色,宋人则相对宽容,“纯白、纯黑、纯黄者不须拣”,若选花猫,只需“身上有花,且四足及尾花缠得过”即可。 吉日、良猫皆定,便要立 “纳猫契”。这份契约并非买卖文书,更像给猫的“安家承诺”:文中既有对猫的期许,如“无息鼠辈从兹捕,不害头牲并六畜,不得偷盗食诸般,日夜在家看守物”;也有相处规则,若猫“擅自离家”,会写“堂前引过受笞鞭” 的戏言;最后还会郑重邀请“东王公与西王母”作见证,并签下主人姓名与日期。侯印国解读道:“与其说这是契约,不如说是给猫的‘婚前契约’,每句话都像在跟猫‘谈心’,把猫当成家里要共同生活的‘贤内助’,满是纪念与祝福的心意。” 仪式的最后一步,是备“聘礼”迎猫入门。宋代文人的聘礼选择,既风雅又贴合生活:南宋诗人陈郁在《得狸奴》中写道 “穿鱼新聘一衔蝉”,“穿鱼”是用柳条串起小鱼作聘礼,“衔蝉”则是当时对猫的雅称——因通体白毛、口边有黑斑的猫形似“衔蝉”,后唐琼华公主最早用此名,渐成通用叫法;而陆游的圈子更偏爱用盐聘猫,他在《赠猫》中写下“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其师曾几也在《乞猫》中提“江茗吴盐雪不如”,用“洁白如雪的上等吴盐”配茶叶作聘礼。
聘猫用盐,取“有缘”之意
为何用盐?清人黄汉在《猫苑》中援引张孟仙的话解释:“吴音读盐为缘,故婚嫁以盐为赠,取‘有缘’之意,聘猫用盐亦是如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盐属官府专卖,价高珍贵——南宋初年盐价约150~200文/斤,而渔民日收入不足百钱,仅能买半斤盐,用盐作聘礼,足见宋人对 “迎猫”的重视。
这种聘猫习俗还一路流传至后世:清代杭州文人高澜在诗中写“漫索晶盐才聘去”,记录用 “上等晶盐”赠猫的习俗;《清稗类钞》则提到,杭州迎猫时会在盐外多加一束毛笔,取“笔”谐音“逼”,寓意“逼鼠避祸”;嘉庆年间周凯的《迎猫》诗也佐证 “裹盐聘狸奴,加以笔一束”的仪式。此外,清代不同地区还衍生出多样聘礼:瓯地用“盐醋”,潮汕用“糖”,绍兴用“苎麻”,甚至有“苎麻换猫”的谚语,黄汉本人聘猫时,还特意备了“黄芝麻、大枣、豆芽”,满含对猫的期许。
若说宋代文人“爱猫成痴”,明代文人则将聘猫仪式推向更周全的境界。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在《乞猫》诗中记录自己的聘猫细节:“遣聘自将盐裹箬,策勋莫道食无鱼”,不仅用箬竹叶包盐作聘礼,还提前备好鱼;更贴心的是,“女郎先已办氍毹”——家中女儿早为小猫缝制了毛毯当居所,这份细致,比宋代的仪式更添了几分温情。
如今,《宴遇永安》通过一场“聘猫礼”,让千年古俗走进观众视野。从宋代的“择日、相猫、立契、备聘”,到明清的习俗延续,古人对猫的珍视,早已超越“捕鼠工具”的定位,化作一份充满生活仪式感的温情——这份跨越时空的“爱猫之心”,或许正是这段剧情能引发共鸣的核心原因。